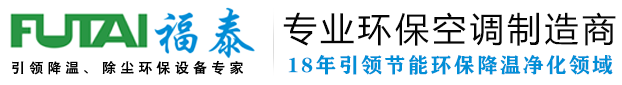?《孫子兵法》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及其對現代戰爭的啟示
羅春華
《孫子兵法》被稱(chēng)為“兵法圣典”,影響中國和世界戰爭史幾千年,至今仍被軍人奉為圭臬。然而,如拘泥古文,囿于舊法,可謂“死讀書(shū)本”。惟有立足現實(shí),汲其精華,方可賦予其活的靈魂。
要學(xué)習掌握《孫子兵法》的思維方式
《孫子兵法》博大精深,不僅是軍事杰作,也被譽(yù)為古代文學(xué)精品,其中不乏美妙絕倫詞句。如“善守者,藏于九地之下,善攻者,動(dòng)于九天之上”“故其疾如風(fēng),其徐如林,侵掠如火,不動(dòng)如山,難知如陰,動(dòng)如雷震”……
讓人感嘆的是每一精妙詞句,又是兵法之要訣,能熟誦其名言警句之人,通常也是深諳兵法之將,一句“攻其無(wú)備,出其不意”,不知創(chuàng )造了多少戰爭奇跡。

當然,語(yǔ)言只是思維方式的外在表現,惟有從語(yǔ)言進(jìn)入科學(xué)思維方式,方可領(lǐng)悟兵法之真諦。正如岳飛所言:“運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。這“一心”即思維方式,幾千年來(lái)將軍智愚之分在“一心”,勝敗成否也在“一心”。
如孫子言:“眾樹(shù)動(dòng)者,來(lái)也;眾草多障者,疑也;鳥(niǎo)起者,伏也;獸駭者,覆也。”講得是從自然和人文現象的細微變化中,發(fā)現敵軍行動(dòng)先兆和企圖。這就告訴我們,觀(guān)察問(wèn)題要由表及里、由此及彼,“察先兆、析過(guò)程、斷結果”,這個(gè)完整的思維鏈,就是邏輯思維方式。只有據此,才能準確判斷情況,正確定下作戰決心。
再如 “攻而必取者,攻其所不守也;守而必固者,守其所不攻也”“投之亡地然而存,陷之死地然后生”“故形人而我無(wú)形,則我專(zhuān)而敵分;我專(zhuān)為一,敵分為十,以十擊其一,則我眾而敵寡”。孫子辯證地分析了攻與守,生與死,專(zhuān)與分、眾與寡的關(guān)系。指揮員如能掌握辯證思維方式,就能揚長(cháng)避短,趨利避害,從而聚寡為眾,由弱變強,能攻善守,穩操勝券。
還如“故智者之慮,必雜于利害。雜于利而務(wù)可信;雜于害而患可解也”“知兵者,動(dòng)而不迷,舉而不窮”“無(wú)恃其不來(lái),恃吾有以待也,無(wú)恃其不攻,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”。意為,任何決策不僅要想到利,更要想到害,而且要考慮可能出現最壞的局面,洞察瞬間變化,這就是底線(xiàn)思維。指揮員把握了底線(xiàn)思維方式,何時(shí)、何地、何情都可立于不敗之地。
當然,作為兵法最為突出而又十分重要的是奇異思維,即非常人之所想,非常人之所為。孫子坦言“兵者,詭道也”,《孫子兵法》就是一部兵家權謀教科書(shū),謀略之深邃,嘆為觀(guān)止。如其言“兵以詐立,以利動(dòng),以分合為變者也”“凡戰者,以正合,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,無(wú)窮如天地,不竭如江河”。凡善于奇思妙想之將,必勝之無(wú)敵,名垂青史。

要不斷適應戰爭形態(tài)的變化
《孫子兵法》之不朽,在于兩千多年前,就站在軍事辯證法的立場(chǎng)上,鮮明地指出戰爭形態(tài)變化及應變策略,使后人能不斷推陳出新,創(chuàng )造地贏(yíng)得戰爭勝利。
其曰“兵形象水”“兵無(wú)常勢,水無(wú)常形”“其戰勝不復,而應形于無(wú)窮”。 形容戰爭形態(tài)像流水一樣不定,加之奇正虛實(shí)相生,其變“如循環(huán)之無(wú)端,孰能窮之?”
戰爭形態(tài)變化無(wú)常,故孫子認為指導戰爭“不可取于鬼神,不可象于事,不可驗于度,必取于人”,這里的“不可象于事”,就是不可類(lèi)推比附,囿于昔戰之法。為此,他特別強調“踐墨隨敵,以決戰事”,“能應敵變化而取勝者,謂之神”,因敵而變,欺敵就范,用兵如神豈有不勝哉!
認識戰爭形態(tài)變化,萬(wàn)不可僅限于戰場(chǎng)上的擺兵布陣和戰法運用,這只是表象??茖W(xué)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帶來(lái)武器裝備的更新,武器裝備的更新,推動(dòng)新型作戰力量的形成,并導致作戰編成、運用方式、保障條件諸因素變化,使戰爭形態(tài)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(shí),由于工業(yè)化的高度發(fā)展,強大的機械化突擊兵團實(shí)施大迂回、大包圍、大聚殲,構成機械化戰爭形態(tài)。而二戰結束后,隨著(zhù)信息、生物、人工智能等科學(xué)技術(shù)高度發(fā)展,這種傳統模式受到嚴重挑戰。

從戰爭思維向大國博弈思維跨越
《孫子兵法》從國家與戰爭的關(guān)系談起,詳述了戰爭及指導的相關(guān)理論。孫子處于春秋末期,周朝已日漸式微,王權旁落,諸候混戰兼并,逐漸演化為數大國之間的博弈。大國博弈主導著(zhù)“天下”戰略格局和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秩序等,決定著(zhù)或和平、或戰爭。孫子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,形成其戰爭藝術(shù)和大國博弈智慧。
兩千多年前,孫子就認為戰爭不是解決國家利益沖突的好方法,故曰“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”“上兵伐謀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,攻城之法為不得已”。最好的方法是以謀制勝,迫不得已才進(jìn)行戰爭。他提出“必以全爭于天下,故兵不頓而利可全”,即:以全勝之計爭天下,不頓兵血刃獲全利,贊譽(yù)“不戰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”。孫子“全勝”的思想,已跳出戰爭思維束縛,“不戰而勝”被戰略家們奉為大國博弈的優(yōu)選策略。
一部《孫子兵法》,給我們提供了戰爭藝術(shù)。其中“屈諸候者以害,役諸候者以業(yè),趨諸候者以利”含義深邃,可為經(jīng)典。
先談“趨諸候者以利”?!妒患易O子》曹操注“令自來(lái)也”。這就告訴我們,授之以利,其必趨近,互惠合作,可免沖突,甚至互為掎角。
再談“役諸候以業(yè)”。“業(yè)”古文同“涅”,意為害怕,所以吳如嵩先生在《孫子兵法淺談》中譯為“靠實(shí)力威服”,古人稱(chēng)為“道勝”或“威勝”,即通過(guò)展示國家堅強的意志和強大的實(shí)力懾服對方。
最后談“屈諸候者以害”?!妒患易O子》梅堯臣注“制之以害則屈也”。大國博弈“利益至上”,對方在軍事上的威懾、侵犯甚至一定規模的戰爭沖突,主要是為了從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外交和軍事上獲得更多利益。
作者簡(jiǎn)介:羅春華,1954年出生,江西南昌人,1972年入伍,歷任班長(cháng)、排長(cháng)、教員、營(yíng)長(cháng),大校軍銜。其間先后在南昌陸軍學(xué)院、南京高級陸軍指揮學(xué)院、國防大學(xué)就讀,并被選送至俄羅斯總參軍事學(xué)院進(jìn)修。2006年轉業(yè)至地方任副廳長(cháng)、巡視員。著(zhù)作有海峽書(shū)局出版的《老兵談孫子兵法》上下冊。